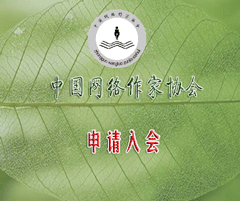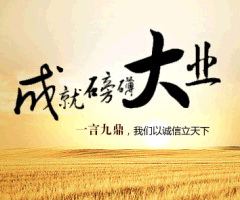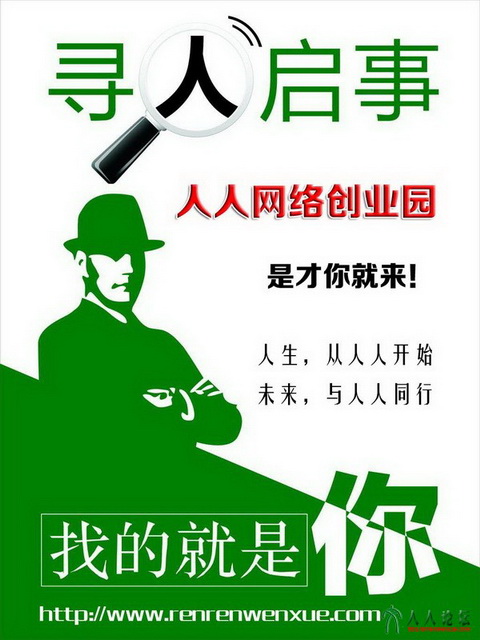|
进藏日记 作者:李发祥 一次筹划已久的旅行,一场饥渴已久的文化采风,因为一个意料之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变成一次特殊的旅行。8月7日前为游藏记,8月8日后为抗疫记。——题记 
7月26日 心里盘算了十年,实在准备了数日,后天就要启程,到西藏去! 进藏一游,心仪已久,也不知道那些年忙些什么,总没有成行。前几年又有文友相约几次,各种原因,终未成行。 伟大的祖国疆域辽阔,东南西北风土人情各异,每到一地,总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旅游给人带来的愉悦;而能把旅游目的地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去审美,那将会得到心灵的启迪,这是文化浸润的美妙。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把难得的进藏之旅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白白耗费大半月光阴,那就对不起好心邀约同行的文友,更是对文化二字的亵渎。 所以,这次刁丽俊老师再次发出邀请,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刁老师数年来每年至少一次赴藏,每次都有大作见诸国家级报刊,既介绍西藏风情,又对相关物事作文化探讨,引人入胜而发人深省,对西藏之行热情日盛,已然成隐。此次进蔵她就是专门为探究纹面人群生活而去的。 西藏的概念,小时候的初次印象,是关于运粮援蔵的故事。《昌宁县志》载,1950年10月3日至次年1月4日,昌宁奉命组织200多民工和700多匹精壮骡马组成支援解放西藏民工运输队伍,被保山地区援藏指挥部编为第八、第九大队,由谷子明和张亮分任大队长,从保山领取军粮760驮,经老营、瓦窑、槽涧、旧州、表村、兔娥、营盘、小维西、白济汛、康普、岩凹、叶枝、羊咱,过沧江溜索,翻越四望雪山,抵西藏门工交付军粮任务。返回来的途中,还帮助保山县第一、第二大队从雪山东麓粮站运送230驮军粮再抵门工。两次运粮共990驮3.96万公斤。为此,荣获集体一等功。自此以后,昌宁人说话老实、做人诚实、办事踏实的“三实”作风和“一根丝”精神,就成了昌宁和昌宁人的文化标签,广为传颂。 再后来,从地理课本上知道,青藏高原乃世界屋脊,雄伟辽阔,华夏大地山脉多发于此,如万马奔腾涌四方,江河湖海多发源于此,有世间无水不朝东之说。于是,对青藏高原的向往油然而生,只不过,自己还不是那只勇敢的雄鹰。 再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了,信息流也多了起来,报纸、广播上的新闻也见了些,但总会在关于雪山、草原、戈壁、沙漠、牦牛、骆驼等这些物象之间徘徊,也会在宗教、庙宇、朝圣等未知领域中想象,还对青稞酒和蘇油茶产生了神往,但真正喝到青稞酒和蘇油茶,那又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电视的普及,坐堂看世界,尽知天下事,对西藏的认知逐步清晰起来,向往之情也与日俱增。后来听一些朋友讲他们的进藏感受,或山野高峰,或旷远大漠,或雪山雄鹰,或草原牛羊,不一而足。也难怪,我想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西藏印象,他们聊的,是自己心中的西藏,或是他们自己经历的西藏,准确的说,是其中一部分或一个片断。忽然明白,我需要一场更高层次的对话,那就是到西藏去,自己亲身去体会西藏。 催生向往西藏情愫的,还有那些余音绕梁的音乐和歌曲。一曲《天国的女儿》让天上的冰雪不忍化落,终成屹立亘古的雪峰;一首《天路》唱出时世变迁,给人有了去西藏不像登高原,而是如履平地散步赏景的感觉。虽未进藏,西藏印象已沉淀心底,旋律激荡心灵。西藏之行,势在必行。 
7月28日 我们的导游兼司机叫德拉姆玛璜,大家都称呼他为“玛哥”。刁老师与他一起来住处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去接住在保山城的其他几位旅友,最后在高速公路入口处接从腾冲赶来的赵兴科老师,沿着保大高速,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后来的交谈中得知,玛哥在大西北跑了二十多年,对整个大西北都熟悉,八条进藏线路及沿线大小城市集镇均有不同程度了解。德拉姆玛璜是藏语名,德拉姆为神居之地,玛璜为神仙所用之剑,据说是某位高僧所名。 赵兴科老师是前不久省作协会员培训班上认识的,之前读过他的文章和诗歌,时隔不久即又同行,当是缘份。 另外两名老师兰朝花和赵会星,是一对姑嫂,刁老师的好朋友,看上去几位女士年纪相仿。 旅团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叫阿畅的学生,真名张秦畅,刚满十八岁,高考结束。 都是文学爱好者。刁老师是知名记者和作家,自不必说。另外两位女士不大参与谈论文学文艺话题,但对于旅行、美食、购物等很感兴趣,于文学而言,更多的是谦虚和神秘。赵兴科老师是腾冲文艺界后起之秀,声名已望。阿畅的妈妈在送他上车时,很客气地说请大家照顾他,多担待,可刁老师介绍时,说他是一个喜爱文学的青年学生。 沿途看到修建多年、因地质结构复杂而迟迟未能通车、早已成为风景的大瑞铁路过山高架,大家的话题自然集中到上周(7月22日)的大瑞铁路通车仪式上来。刁老师介绍说,市文联正在筹备一期大瑞铁路专刊,安排赵兴科老师和我写点东西,我俩欣然接受了。瞧,专业加上敬业,真是职业病带重了。或许,这就是文艺(文化)工作需要坚持坚守的缘故吧。看似旅游的一次行程,看来,还得用文化理念来解读。 一路上刁老师深情地回忆数次进藏经历,德拉姆玛璜串讲了藏族聚居区一些逸闻趣事,气氛很好。 不知什么时候,话题转到海男的诗歌。热烈的讨论概括起来三层意思:一是海男的诗歌语言很特别,一些词语叫“想得起”,已打通了她与世界、与神灵、与天地的沟通,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自带光环的意象体系。我们不在乎读懂与否,而只能默默地仰望。她的诗歌语言属于她的立场,别人是学不来慕仿不了的。二是学写大散文,选题要准,构架要得当,表达要丰富,要有厚重感,反映大时代中的社会生活内容,突出人性的温暖。充分考虑时代背景,跨时代的要有时空纵深感。三是小说散文化和散文小说化是大趋势,要学会讲故事,把故事讲精彩。 瞧,俨然一堂培训课。 虽然还早一点,只有住丽江。主要是进藏前须做核酸检测,等结果,明天到德钦,路途较远。 丽江是20世纪90年代就来过了,那次是携爱人一起来的。除了丽江玉龙雪山的美景和古城四方街,留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纳西传统文化。特别幸运的是,当时大研古乐馆仅两百多个座位,票早已销售一空。那时各方面条件有限,馆方知道我们大老远几天转数次班车慕名而来,第二天凌晨又要走,实属不易,特地找了条凳,让我们坐在通道上欣赏洞经古乐表演。文化名人宣科亲自主持,用标准流利的英汉同步主持,对纳西文化的介绍绘声绘色,张养浩的《山坡羊》,大唐遗音、相传为唐玄宗所作、《霓裳羽衣曲》的姊妹篇《霓裳羽衣舞》,经典古乐破冰尘封的时空,洞穿肺腑,震颤心弦,荡涤心灵,至今回荡在心间,记忆犹新。关于对东巴文化前世今生的更深认知,就是从这次演出结束时宣科先生签名售书《宣科与纳西古乐》中了解的。 
7月29日 早餐后在丽江市人民医院做过核酸检测,就上路了。 “邃道密集”的标识牌迎面接踵而来,山势高大陡峭起来,植被逐渐异样,与滇南滇西南区别明显,思茅松渐次隐匿,云南松成为主角,山坡地面裸露的地方多了起来。占全线约八成的隧道过完后,进入小中甸,过香格里拉西侧继续前行。香格里拉大家都来过了,与依拉草原和纳帕海匆匆告别,沿茶马古道,即国道214线北行。 沿金沙江岸边逆行,在奔子栏用午餐。这里曾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会师后挥师北上的关隘,为红色旅游圣地。这一带地形地貌大为迥异,两岸山岩如刀劈斧凿,几近垂直,寨子不大,挤在沙滩高丘地带,有的三两户挂在山腰间,树木草丛稀疏可怜。玛哥听到我们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轻轻一笑,说这两天,我们都是在这样的狭谷环境中疾驰,奔子栏这个小镇,算是人口较为集中的了。 又上坡了,翻越白马雪山,这也是此行进藏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本想好好欣赏沿途景致,却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已过山丫,正在下山。突如其来的山雨迫使车辆放慢速度,路面已结冰打滑,路面被车轮扎得脆响,汽车挡风玻璃上都蒙了一层薄冰,不得不开暖气空调化解排湿。个个都屏息凝气,没有了话语。还好,有惊无险。 “快到观景台了”,玛哥的提醒打破了一时的沉默,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了山高坡陡、路窄弯急和天气的急剧变化,顺着他手指方向,我们见到了侧露面容的梅里雪山。 停下来时,惊奇的一幕出现了:约五十平方米的观景台,稀稀落落的几点雨,后面来时的路被中雨全部浇湿,水流横路,而观景台前面的路道干爽,没有下雨。阳光隐在云中,远望梅里雪山在浓淡不定的山雾中犹抱琵琶半遮脸,神女峰身披面纱,五指峰时隐时现,其它冰川不见峰顶,主峰卡瓦格博更是不现首尾。我们就是在这场不大不小的太阳雨中与梅里雪山初次见面,抢拍她的羞涩。接下来的行程中也数次拍摄,但终究角度不一,特别是雾气升腾移动的感觉,再也不见这番景致。 一头扎进梅里雪山的怀抱,缘澜沧江两岸而上,在约五十米宽的夹缝中变幻着相同的景色,垂直的两岸展露亘古不变的姿势,亿万斯年而不朽,江水咆哮奔腾不息,高山陡立突兀,随着车子前行而移步换景,险峻迎面撞击眼球,山坡和岩石用禇红、深褐、浅黄、灰玄的色调变换音符,回应着江水空谷的轰鸣,远处山峰白雪皑皑,天空高旷深蓝,形成一幅自成特色的苍凉画面,偶尔见从山顶垂直而下的雪山溪流如白练鞭僻大山,纵贯山顶达谷底,给人以动感之美。 有水的地方才有人居住,这些村庄散布在江边两岸,与树木和庄稼地的绿色融为一体,形成绿洲,与周边山坡岩石颜色形成巨大的反差,极富生命的温暖感人情怀地点缀着这方山水人文。这些绿洲也不大,大多数亩数十亩的样子,村庄居户多少依悬崖下台地面积大小而定,让人禁不住想起那句“寸土寸金”的老话,惊叹大自然的苛刻,更惊异和叹服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要以怎样的坚毅、勇敢和乐观,去凿穿岩石,翻越高山,跨越江河,与外部环境实现完美对话? 黄昏时分,抵达盐井。临街旅店和餐馆顺路铺开,我们吃、住的两家店主,都是保山人,这也算是一种缘份吧。 盐井,这个因产盐而闻名的地方,在茶马互市的年代独树一帜,作为生活必需品,食盐自古就是商贸中的骄子,有些时候甚至贵比黄金。遗留的千年盐井和盐田见证过曾经的辉煌过往,岁月沧桑,马帮铃声终抵不过汽车的马达,只有江水,涛声依旧。 
7月30日 继续在高山峡谷中穿行。江河切割的山川,让人自感渺小,虽各自成景,令人惊叹,但让人不得不盘山开路,盘旋上下。今天至少要翻越五座大山,于是,大半天的行程就在上山-下山-上山-下山的周而复始中徘徊。 首先翻越红拉山。海拔4448米。大家在冷风嗖嗖中留了影,打卡后继续前行。玛哥告诉我们,我们自此告別身后的澜沧江,向西向怒江上游支流区域进发。遗憾的是,翻越后来几座雪山时,我沉沉地睡去了,醒来的时候,见到地貌变得青葱了些,高山杜鹃、青钢栗、青杨依次变幻着道场,不久后又渐次隐没,草原逐步成为主角。 海拔5130米的达拉山丫口,公路离山峰峰顶只有百米左右,雪线沿山脊一字排开,一眼望不到边,盛夏雪融,雪线上全是裸露的岩石,一年中只有夏季这几个月见真容,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大雪覆盖。雪线下隐隐约约的绿色,野草顽强地抗争,越往下,绿色越浓稠,到山脚下的小河边,往往成为绿洲或牧场,三五顶帐篷炊烟袅袅,牦牛数头数十头嵌在河边或挂在半山坡草地上,红的黄的野花铺成地毯,也不知道牛们是吃花还是啃草,抑或是既吃花又啃草,雨雾中看不真切。 汽车沿玉曲河一路向西,走走停停,边走边拍,拍完再走。不知谁引发的话题,行进的车辆中一度陷入关于人的前世今生以及人是否有转世未来的争论,内容涉及到哲学、生命科学、宗教等,不亦乐乎。由于观点偏激,谁也说服不了谁,又不必要一定要去说服谁,没人在意中停止了争论。不知不觉地,进入邦达草原。 广阔的草原上,远方绵延的山峰拥着长长的绿毯,玉曲河在中间缓缓流淌,河两岸藏民村庄、青稞地和牧场错落分布,蓝天白云,露脊的山峰,雪线,稀疏的植被,草坡,牧场,河流,由上而下的空间分布,一目了然,三江源的腹地,纯净得像一幅画。 该晚住邦达。晚餐是牛肉火锅煮松茸。几位女士在路过芒康时专门到农贸市场买鲜松茸,果然比我们那里便宜很多。除了口头零食和水果,刁老师还准备了咖啡和功夫茶,在动荡的车子上,小心地为我们沏咖啡、泡功夫茶,令人感动。 
7月31日 随着行程的推进,我们离开了横断山区,进入藏北高原深处。翻越的雪山越来越高,草原也更辽阔,更广袤。 路过洛隆县城时已是午后,为节省时间,我们在街边以一碗“老麻抄手”打发午饭。城管的来了,我们不知道此路段禁止停车,问明情况后,安慰说“不急,慢慢吃,吃完了再走”,如此人性化执法,令人汗颜而感动。 去三色湖的路还很远。在高山狭谷中穿行大约二百公里后,终于见到边坝县冰川脚下的湖:其实是一条高山冰川雪融河,随河岸地势宽窄不平而自成形状各异的湖泊河湾,又因当地土质岩石所含金属成份不同,加之阴晴不定或早午晚日光强弱和照射角度不同,导致湖水颜色发生变化,在静止水湾水面呈浅红、微黄和深蓝三种颜色,故称“三色湖”。而冰川湖即是整条河和三色湖的源头。 我对三色湖并不感到神秘,却对尚未融化的冰川肃然起敬。镜头掠过湖面一块浮冰直指雪峰,雪风迎面送爽,让人舟车劳顿的疲惫倏然消散,神清气爽。 捡到一块不规整的石头,略成三角椎体,亚麻布石类,十分干净,暗纹线条呈等高线分布,颜色和形状与周边石子略异,姑且称“三色石”吧。我双手轻抄湖水,轻轻浴洗,准备带走。正在这时,电话响了,儿子告诉我,他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被云南艺术学院录取,于是赋诗一首,以记巧事,当天即刷爆朋友圈,后来收入《高原组诗60首》中。 雪山之巅的修炼 难成正果 冰雪尘封的岁月 期盼一缕阳光 雪崩 一粒石子 奉神的旨意 随冰川跌落 你在湖边 打磨千古不变的爱情 我来了 轻抄湖水 为你洗泪洗尘洗心 拥你入怀 佛说 缘份已到 
8月1日 从边坝县城出发到比如县的路,翻越的山越来越高,峡谷越来越深,草场或大或小变换着频率,景色也更丰富神奇。时不时有路边观景台,挤满了拍照的自驾游客。公路在向前延伸,保通标志、公路水毁路段标志、水毁路基沉陷标志频繁出现,抢险保通队伍时常遇见。高山狭谷地貌的交通,附属工程太大,有些工程体量如山,直接超乎人的想像,偶有飞石落下或洒满路面,我们很幸运,没有被撞到。交通标识中雪线路标表明,这些路段全年大部分时间都被冰雪覆盖。 海拔4500米以上,树木退出舞台,只有裸岩、冰川和冻。冻土层厚三至五厘米,最厚不会超过十厘米,披着地衣植物,一些牦牛不畏山高坡陡,“挂”在山坡上觅食,趔趄得让人胆颤心惊。 在怒江第一湾的观景台,人造悬空天桥,距江面近二千米,令人两腿发软,尽管沿江的村子、远山雪峰、裸露的红岩、弯弯的江水,以及远近不同角度的景致,均被收入我们的镜头中,但上岸落地后,仍有劫后余生的恐惧。 茶曲河,是怒江的上游,今晚在度曲乡打尖。乡政府驻地往前1公里,“怒江缘•文成公主广场”值得徜徉。与之毗邻的达姆寺,相传为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小住,为答谢地方僧侣和民众供养,委托“伦布(即政教合一的地方行政长官)”修建,比拉萨的大昭寺还早。那些残垣断壁的僧舍,早已成为被保护的文物。 另一个与其它大多数寺庙不同的是,寺中还有一个天葬台。时已黄昏,一名喇嘛见我们跋涉几千公里而来,破例地在下班后准许我们参观了骷髅墙,并现场给我们讲了天葬的过程及仪式,还恩准我们拍照,这让我们大感意外又心存感激。 看骷髅墙,听了天葬习俗,让人对藏民死后尸首喂兀鹫的做法毛骨悚然,也会颠覆人的生死观。 藏人信奉自然,敬畏神灵,注重今生,向往来生,坚信生前行善诵经能为自己来生转世积德,能进入理想的天国重生死后主要是天葬和水葬。说得直白点,就是死后由天葬师大卸八块喂兀鹫或喂江鱼。而且,剁得越细碎,超度越快,通往来生的路更顺畅,痛苦更小,下一世更幸福。 当晚在达姆寺对面茶曲河对岸、当地唯一一家宾馆住宿。“比如县公主温泉康养中心”规模不小,住宿客人不多,舒适清静。 
8月2日
从度曲的公主温泉康养中心启程,向班戈前进。山峰更远更连绵,草原更广袤渺远,牛群和羊群规模更大,时不时有大景,停下来欣赏拍摄。要么是湖泊如镜,嵌在绿色草原中,与远山和天际之蓝形成三色对比图,有的与裸岩构成五色梯次对比图,十分壮观。要么是形状奇异多彩的云,舞动在笔直的道路尽头,望不到天边,汽车像在云层上行走。一整天,都在穿越羌塘大草原的途中。大景美景让人审美疲劳。 途中一处离公路约十来米远的地方,一大群兀鹫正在撕扯一头死去的牦牛,腐味熏人。许多过往车辆都停下来,游客纷纷抢镜,只为平时难得拍到兀鹫的踪影。 其它的景色雷同,疲倦袭来,竟长时间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是旅伴们惊呼着拍藏羚羊了。三只幼羊在公路边吃草,不远处游荡着两群绵羊。透过车窗静静地拍,玛哥说,别下车,人一下车,藏羚羊就跑了。与藏野驴一样,藏羚羊也属于保护对象。 
8月3日 事后才知道,穿越羌塘草原需要几天时间,这是我国第四大草原。准确的说,这几天我们只能穿越小半个羌塘。汽车高速飞驰在大草原上,神思飘逸,不禁让人想起“一眼望不到边......”的歌声来。 羌塘草原最大看点,是“一错再错”。错或措,是藏语音译,意为“湖”。因无数大大小小的湖泊,沿途接二连三,故戏称“一错再错”。沿途有牦牛群和绵羊群,偶尔见三两顶帐篷,倒是藏野驴和藏羚羊频繁出现,除了这些,大部分属无人区,离公路更远些的地方有狼和藏狐。我们没空也没胆量去招惹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以色林措为主的高山雪融湖泊群,尽可大饱眼福。湛蓝的天空下,几朵白云悠悠飘在极目处,皑皑的雪峰点缀着画面,远远近近的山坡和草地连着浩大的湖水,湖面映漾着云彩和山峰倒影,自然的五色景观,五条线分明横切,割出宏大的画面,无需构图,随手拍来都是大景美景。最壮观的,还是云彩的移动,渲染着湖水,有时甚至觉得湖水也在移动。在深蓝的背景底色里,用金色、银色、湛蓝、浅蓝、淡绿、浅白、绯红等不同色调变幻着,禁不住去抢镜头,可有时这种变化太快,快到难以捕捉的地步,尤其是在不远处忽雨忽晴的时候。 这个西藏第一全国第二大的咸水湖,面积2391平方公里,仅以一天时间从其一角路过,要想表达出她的迷人景致和文化底蕴,我的文字注定是惨白无力的了。难怪有人说,看了色林措,就不再有看湖的兴致,甚至,连看海的兴趣都没有了。 隔着色林措看冈底斯山脉,绵延无尽,虽看似近在咫尺,实则不止百里。 当晚在尼玛县城打尖,晚餐主菜是炕锅羊肉,因菜单打成“坑锅羊肉”,旅友戏称“坑爹羊肉”,遂现场作打油诗一首以记之: 在尼玛街 我们点了一个 炕锅羊肉 菜单打错了 坑锅羊肉 旅友戏言 坑爹羊肉 连起来读 就是 在尼玛的街吃坑爹的羊肉 那是最正宗的炕锅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