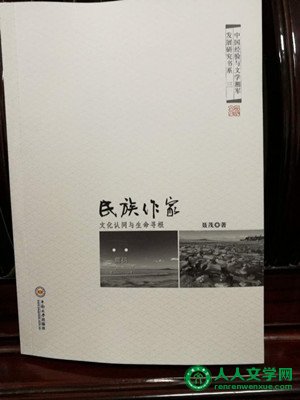 第三节天地之孕:跨文化的底层叙事 帕男的诗歌中多有智慧和哲理的诗篇,也有充满讽刺和幽默的表现世情的精品。《天•地•人》这首诗里说:“人面千种/要读就读眼神/哲人的头颅里/早把眼睛当了窗户/万物递进/逃不过眼睛/眼睛里充斥了真善险恶/休怪眼睛/泪水随意飘洒/惟有面对真人/眼泪才会清纯。”诗人将眼睛写作洞察心灵的窗户,这看似是一个很常见的比喻,可是帕男却将这一意象上升到了哲理范围。他在写唯有面对真人,眼泪才会清纯,但其实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所流出的眼泪都是透明。所以,这里不能仅仅从现实世界出发去看诗人所说的“眼睛”以及“眼泪”,而是要以一种抽象的思维去理解,作者所谓的“眼睛”。在这里眼睛与心灵是合二为一,眼清心自清,心清人自清。所以,真正、美好的情感是由内心而发的。正像诗人所说的人面千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在于外表而是透过表面去看本质。 拉美诗人何塞•马蒂说:“诗是我心灵的一部分,也是我的武器,我的诗没有一首是杜撰的,它就像眼睛里流出来的热泪,伤口中淌出来的鲜血。”[ 何塞·马蒂:《何塞·马蒂诗文选》,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帕男同样如此:“那年月里/是谁不慎/一篙扫落太阳/掉进深潭”诗的这一句写黑暗岁月里,不慎落入黑潭,那里没有一缕阳光照耀。在这种绝望的坏境中,诗人紧接着写到:“黑发是夜的兄弟/是夜走失的帘布/每当充满情绪的头颅晕眩/帘布顿作头帕/让窗无法感受无棂的撑持/俨如无锁的门叶一样柔弱。”在这一节中,诗人采用黑发、帘布、头帕、窗、门叶等意象,紧接着写黑发在黑夜中为眩晕的头颅做帘帕抵御外界的干扰,突然笔锋一转写窗因为没有灵柩的支撑而显得柔弱。诗中写到心灵与现实,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在最黑暗的时光中,是诗歌填满了诗人柔弱的内心。 谢冕先生说,“可以为诗骄傲的是,在所有文学艺术样式中,它最先、最丰富也最全面地保留了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情感的投影。这些投影不同于我们业已熟知的那种全知的描绘与再现,它断然排斥了直接观照的方式,而代之以总体象征性的对于生活、特别是人们内心情感的被动地直述和直描,它是无情的反叛。想在这些诗中寻找关于实际生活的图解与阐析,只能是徒劳。注重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对于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溶解和包容,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谢冕:《朦胧诗选—历史将证明价值》,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在江华瑶族作家群中,叶蔚林是一个旗帜性的作家,他是江华瑶族作家群的峰顶,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江华作家群落的写作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叶蔚林出生于广东惠阳,从部队转业之后定居江华;帕男则出生于江华,现居于彩云之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从生活地点上说,前者的终点是江华,而后者的起点在江华,总之江华给了他们创作的灵气。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叶蔚林的落脚点在江华,作品的精神底色纯净,有较强的归宿感,强调文学要有“根”,《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蓝蓝的木兰溪》、《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都是瑶族人生活方式的化石,是如屠格涅夫一样干净的世界,也是有别于沈从文湘西描写的别样空间,所以湘西的世界在沈从文的文字里,而湘南的世界则在叶蔚林的作品中。 帕男则不同,江华给他的是灵气、血液和感觉,而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和生命的理解在流浪中完成,从湖南江华到云南楚雄,他从未走进文学圈子中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从边缘到边缘,从中南到西南,无论从地理意义上,还是文化意义上,他总是在边缘,但是在文学意义上,边缘并非是一个落后的代名词。帕男的文学创作从诗歌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他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转换成诗歌,遂结成了最初的诗集《男性高原》,之后,200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诗集《落叶与鸟》,诗集《帕男诗选》《落花,是一个旧时代的禅让》《只有水不需要剃度》《在云南在》《等我驾到》和《第三十七只兽的阵亡》。 纯文学的大部分作品离不开三种文体:诗歌、小说和散文,这是纯文学领域的基石,只有在这些领域的成就才可以标举造诣,因此中国作家纷纷以纯文学作为自己对艺术追求的侧影,而对于直接把文学虚拟性和新闻写实性结合在一起的报告文学则较为排斥,这也成为报告文学不够纯粹的口实。作为一个诗人,帕男在报告文学领域颇有建树,1996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高原潮》,1999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阳光地带》,长篇纪实文学《裂地惊天》,2004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穿过神话之门》,2016年由云南民族出版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芳泽无加》《大江歌罢》和《格局》;另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梦断天堂路》《大冲刺》等,在并不以报告文学为主打文体的作家中堪称奇迹,他是诗人中最好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中最好的诗人之一。读他的诗歌,你能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气息,对黑暗的批判、讽刺和嘲弄从来不吝笔墨,不在意强烈的主观情绪是否影响了诗意的建构,他的灵魂镜面中容不下一丝黑暗的斑点,眼里容不下一颗滞涩的沙子,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因为他的灵魂过于纯粹。 流浪是帕男艺术生命的关键词,据帕男本人讲,他每次在街上听见流浪者这首歌都眼睛湿润,眼圈发红,“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过了多少年华?”帕男的文学影响和成就不会让他居无定所,但是精神的流浪让帕男总是能够在歌声中感受到发自心灵深处感叹。他不会觉得自己属于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归宿,或者在精神上为灵魂寻找依托和慰藉,而是把精神和灵魂放置在众生的喜悦和苦痛、束缚和解脱、浮躁和入定的混乱状态中。 与帕男的创作文体相对应,他的身份随之变化,记者、诗人、作家、行政官员,抑或文化名流,但是这些外在的符号无法改变帕男的自我放逐心态。俄罗斯作家是自我放逐精神中最为集中的群体,他们经常自甘自愿地把自己放在命运的十字架上,为了真理、平等和自由奔走呼喊,很多人被沙皇流放到北高加索等人烟稀少的极寒地区,自生自灭,让诗人们的肉体在蚀骨的寒风和暴雪中逐渐失去温度,在那里,你看不见烟火,看不见灯光,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教堂,只有萧索的树木和皑皑的白雪,你想自由,就让你在无拘束的环境中死去,但是诗人们依然坚定前行,在那样的环境中写下了直击灵魂的文字,冰天雪地盖不住诗歌的优雅,沙皇也不能。帕男也有流浪的心态,但是与俄罗斯诗人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同,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人文水平和人权状况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非常稳定。国家不幸诗家幸,乱世出诗人,俄罗斯恶劣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诗人。作为诗人的帕男知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诗人,需要作家的批判和思考,冷峻的眼光和中肯的声音永远是民族内省的动力,无论世事怎样变迁,真正的诗人永远不会多余,关键在于诗人是否能够站在边缘审视时代,给民族泼去清静的冷水,让民众保持清醒的神志。这与时代是否繁荣无关,与国家是否强盛无涉,保持对社会的真切触摸,对生活深刻感悟……保持流浪的心态,就保持了诗人的存在价值,保持了对社会责任的始终不渝。 因此帕男的自我放逐和流浪心态并非源于对社会的整体性印象,而仅仅是诗人的本能和担当,选择了文学,选择了诗歌,就选择了与现实为敌。更重要的是,帕男的这种心态是在一段自我与时代的纠结中形成的。经历是作家风格的基石,帕男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少年时期正好与狂风暴雨的文革重合,尽管在穷困的僻壤,彼时的江华同样与时代同步,公平被遮盖,民主被荒废,人权被弃掷,这样环境注定了帕男多舛的命运。帕男五岁那年就被送进了乡村小学,原因是父母亲没有时间在家里看护孩子,还不如送到学校里去。彼时的湘南比其他农村还要穷困,而且江华属多山地区,帕男每天上学都要带上那个沉重的松木板凳,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否则容易丢失。在那个物质稀缺的时代,家庭的任何器物都是珍贵的,一个只有五岁的孩子只能按照现行的时代路辙和物质水平生活,懵懵懂懂地融入到了那个不知所以的时代里。家长要“抓革命,促生产”,哪有闲暇去管孩子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学会了自治,哥姐拖着弟妹一起上学,放学之后领着弟妹一路回家。苦与不苦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段尽管艰难却充满了田园牧歌的儿时回忆。帕男在家中排行第二,仅仅大帕男几岁的姐姐,要和父母下田种地,自己就要带着弟弟妹妹,每天早上早早起床烧菜、做饭、穿衣。那时帕男仅仅10岁,刚刚进入初中。从家到学校的路有三、四公里,中间山路夹着河流,离家远了,路程难了,上山下坡就不再是田园牧歌,而是苦难。 如果仅仅是这种自然条件的恶劣,也很难在帕男的心理上烙下深刻的印记。命运的转折总是和升学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场胜负常常成为人生的重要转折,或者没有走上科场就折戟沉沙,或者在科场上失意落魄,或者在科场夺魁后“一日看尽长安花”,总之科场成败决定士子命运,而帕男连上科场的机会都没有得到。1978年,帕男初中毕业,这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之前还是文革的滚滚洪流,之后就迅速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度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那也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时期,旧体制已经瓦解,新制度尚未稳固,莫名其妙中被剥夺了上学权力的帕男并不甘心,父亲到处申冤,却无疾而终,自己到县城讨说法,却不知道跟谁说理去。跑遍整个县城,双脚磨出鲜血,却只能重新复读,而这也是经过了苦苦抗争之后的最好结局。短暂的等待之后,中国迎来了高考制度的重启,推荐制被废弃,从上到下全面推行考试制度,帕男也就顺理成章地读上了高中。高考成绩仅差几分,与大学擦肩而过,只好重新回到农村。这种经历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基本一致,拼命劳动挣工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是一个从官场回归田园的知识分子,也许这是一种难得的情景,毕竟有人白天辞官去,有人星夜赶科场。对于年轻的帕男来说,精彩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他不可能在这样的重复中消磨,知识改变命运,时代的主题、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化与帕男彼时的心境形成了高度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帕男对人生、对世界、对社会有了崭新的认识,看到社会的不公,审视人性的丑恶,成为帕男作品的主调。与公办院校的擦肩并没有让帕男就此失去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在私立大学还是一个陌生概念的时期,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就开始创办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这给了帕男重新读书的希望。九嶷山学院设在湘南九嶷山区的舜源峰下,四围均为山林,学院矗立其中,仅一条蜿蜒于山间的小路通向山外,犹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自然环境十分清静,但是办学条件也非常艰苦,教室是文革之后留下的破庙,墙壁四处漏风,院长办公室是一个被隔板围成的小屋,还要兼当宿舍,女生宿舍同样在这个破庙,男生宿舍在远离教学地点七八公里的地方。这种办学方式与战时的西南联大非常相似。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辉煌的顶峰,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由于日本占领了华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的师生到云南的昆明办学,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但是由于大师云集,战时的艰苦条件并没有成为阻碍西南联大培养优秀人才的问题,相反在之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各方面的顶级大师都源自这里。也许正式由于战时的缝隙让师生们更加珍惜教育的来之不易。在那个时候,日本的飞机经常光顾昆明,师生们在两个校区上学时,经常在路上遭遇飞机炮火的硝烟,听见轰鸣声,趴下躲避,之后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到教室上课。九嶷山学院并未产生在战时的环境中,但是在封闭、落后、贫穷的山区,帕男和他的同学们依然找到了知识的快乐。那里没有城市的喧闹、繁华和便捷,师生们上课条件就是一盏煤油灯、一份讲义夹、一张小板凳,而这些已经足够。南方的多雨连绵培育了文人的细腻,也滋养了女人的温柔,但当屋漏碰上连阴雨,感觉还要雨临头,一切的风景和浪漫都一扫而空。条件不会因为你的厌烦而收敛,无论痛苦与否,它就在那里;无论接受与否,它也在那里,于是,帕男和他的同学们就不再郁闷,学生们都背着蓑衣,头顶斗笠,依然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 苦中作乐是对抗不利环境的最有效的办法,没有现实的安逸,没有可口的饭菜,精神食量总是应该有的,学校是精神食量最丰富的地方,颜回不是也“一瓢饮,一箪食”吗,古人尚且如此,自己当然也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让他们战胜苦难,“立言、立德”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忘记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没有失去人生的航向;“修身齐家”以传统儒家思想的个人修养准则为这些青年人树立了典范。所以纵使吃不饱肚子,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都要翻阅几座山头到集市上去买,阴雨连绵时几乎断炊,帕男和他的老师同学们反而乐在其中,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中支撑到毕业,这也是帕男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从未丧失人生理想的重要原因,他的作品也因此而更加扎实,对现实的批判没有虚空的说教,对理想的追求没有扭捏的矫情。 作品境界从苦难中来,从经历中来,也从精神的煎熬中来。他曾经到中国二汽所在地湖北十堰当一名教师,但很快发现,这里并不是自己的最终归宿,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了讲台。之后他到了十堰电台,满腔的热情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但是他知道这也许是最符合自己的职业,能把自己的爱好、专长和生存完美地结合起来。但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莫名其妙的人事调动让帕男无所适从,在那个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历史时期,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选材用人科学性水平还很低,离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之后的颠沛流离是帕男对人世苍凉和人情冷暖的理念发生质变的时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内蒙,那张民办院校的毕业证无法给他带来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可靠的生计,能力和现状之间的疏离并没有让帕男感到文字的无力,相反,这种流落成就了诗人之幸。在此之后,帕男开始逐渐摆脱生存的困扰,不用为了生存而屈膝,他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写作方向。多年的漂泊沉淀了他进一步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全部积累,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有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召唤这个为诗歌而生的作家。17年来对云南高原的全部感情需要一个途径喷发出来,需要诗行凝固下来,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帕男的第一本诗集《男性高原》,被认为是“对云南高原诗坛不小的贡献。” 尽管真正为帕男留下文坛坐标的依然是新闻性的稿件,通讯《红土地向你出示黄牌》被评为第四届全国地市报好新闻二等奖,编辑作品在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地市报好新闻评选中获奖,本人获编辑奖;长篇通讯《背负哀牢》、《星宿情缘》、《山魂》分获全国记协、中国作协联合举办的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华大地之光”征文评比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新闻论文《走进读者 未必远离党性》获第五届“中华大地之光”征文三等奖;《山里的女人》、《活祭》分别获得首届、第三届全国“箫韶杯”文学大奖赛一等奖、优秀奖,还有《这也是一片爱的土地》获第四届云南省新闻奖等等。另有近20件作品入选《跨世纪一代的足迹》、《流淌的金沙江》、《全国地市报好新闻选》、《中华大地之光获奖新闻选》等10多个选本。 帕男的艺术创造没有因为文体的区分而把自己归属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他的文学才情在诗歌之外的领域依然熠熠夺目,长篇小说《爱过了就分手》、《墙外佳人笑》展示了帕男对长篇小说的构制能力。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爬行和思索之后,帕男开始转向散文的创作,从次序上讲,这是很反常规的,因为首先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对语言控制能力、意境构制能力和音乐感知能力的要求最高。文学的极致是诗歌,但帕男的文学创作从诗歌开始,反而在文坛耕耘二十余载之后才有散文集问世,甚至报告文学的创作时间也在诗歌之后。对于帕男来说诗歌是“自己的园地”,如周作人一样喝苦茶,听冷雨,看风起,只是情趣不同,意境不同,都是作家精神的后花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不似诗歌那样精雕细琢,也不似小说那样工于机巧,更不像报告文学那样直击现实,而是在褪尽繁华之后的深沉,放下一切技巧和构思,它仅仅是感情的凝聚和灵魂的物化,因此帕男的散文显得最为厚实。2003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多情的火把花》,长卷散文《天地之孕》、长卷散文《魂牵五台》(合著),2010年5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一抹秋红》、2011年4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长卷散文《一个皇帝出家的地方》、2017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俚语湘南》、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卷散文《火之韵》。  聂茂,原名陈庆云。曾长期在媒体一线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99年3月出国留学,2003年8月取得博士学位,2004年被中南大学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同年9月由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学科带头人。现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文化学与文化产业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视觉艺术评论委会员副会长,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首批湖南省“三百文艺人才工程“入选者,鲁迅文学奖评委,等等。 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或观点摘要10余篇(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主持省社科基金课题3项(含重大课题1项),主持其他各类省部级项目8项,出版学术著作5部,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文艺报》曾在《学科带头人》专栏头条进行重点推介,《中国文化报》和凤凰卫视等为其学术成就进行过报道。 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全过程,1989年进入鲁迅文学院深造,与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虹影等人为同学。从1992年至1998年连续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学作品,曾获1998年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全国报纸副刊金奖和《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1949-1994)优秀散文奖,与冰心、周涛分列前三名。作品入选《小说月报》《散文选刊》《读者》《青年文摘》和其他书籍与选报选刊达70多篇(次)。出版长篇小说3部,散文集6部、诗集2部、报告文学2部、传记文学4部和翻译作品1部。《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湖南日报》以及湖南卫视等主流媒体对其文学成就进行过报道,多家学术期刊对其作品进行专题研究,并先后有10余名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将其作品列入研究对象。 近年来,教学之余,全部精力聚焦在《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的书写和打磨上,该课题最终成果为6卷本书系,共计240余万字,分别是:《湘军点将:世界视野与湖湘气派》、《官场小说:精神逼宫与灵魂拷问》、《国族经验:个人言说与集体救赎》、《人民文学:现实世界与理想情怀》、《江华作家:民族认同与文化记忆》和《阎真作品:此岸烛照与彼岸原乡》,已由出版社隆重出版。  作品年谱: 诗集《男性高原》(1995年,云南民族出版社) 报告文学集《高原潮》(199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报告文学集《阳光地带》(199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诗集《落叶与鸟》(200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多情的火把花》(2003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长篇报告文学文学《裂地惊天》(2003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报告文学《穿过神话之门》(2004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长卷散文《天地之孕》(2004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长卷散文《魂牵五台》(合著)(2004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一抹秋红》(2010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诗集《帕男诗选》(2010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长卷散文《一个皇帝出家的地方》(2011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火之韵》(合著)(201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长卷散文《滇,我的那个云南》(201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俚语湘南》(201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诗集《落花,正是一个旧时代的禅让 》(2015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即将出版作品 诗集《只有水不需要剃度》 诗集《在云南在》 诗集《等我驾到》 长篇报告文学《芳菲不加》 长篇报告文学《大江歌罢》 诗歌影响 云南楚雄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十分活跃,现已形成了上规模而且相对固定的诗会有“我与春天有个约会·楚雄诗会”、《37°C诗刊》诗会、双柏“查姆诗会”、姚安“荷花诗会”,也被云南诗坛称之为“滇中四大诗会”。“我与春天有个约会·楚雄诗会”是每年一届,全国性的诗会,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举办了9届;《37°C诗刊》今年创立,年内已成功举办了3次全省性诗会;双柏“查姆诗会”亦为一年一届,也已经地举办了3届,姚安荷花诗会今年始创,举办了首届诗会。 以帕男为领航者的楚雄诗坛,号召和团结了一批活跃在当下楚雄诗坛乃至州外的诗人们,正以团队的力量,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出楚雄、走向云南,走向全国,成为了中国诗歌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一批诗歌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火星》、《海外文摘》、《边疆文学》、《滇池》、《云南日报》等大报大刊。 近两年来,帕男创作了两千多首诗作,被著名文学评论家苗洪跟踪研究三年,特地撰写了《一个瑶人的圣经·帕男诗传》、《中国诗歌的通古斯大爆炸与告别韬光养晦的帕男》和《致命的失语与觉悟·帕男论》三部专著;中南大学聂茂博士为其撰写了《文学场域中的民族书写·帕男论》;20多位评论家集体撰写了《帕男的N个面》(评论集),这一现象在中国诗坛较为鲜见。 |




